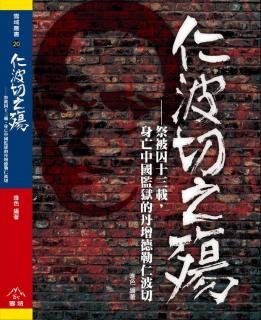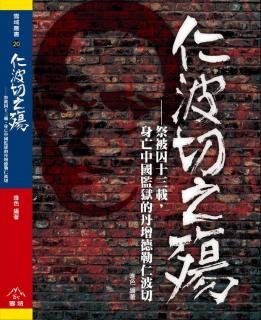丹增德勒仁波切案2002-2003年日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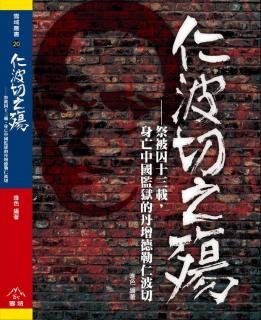
2002年12月13日
•建議書
上午,王力雄將關於阿安紮西、洛讓鄧珠死刑案上訴審理的建議書列印了三份,要寄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並在每一份末尾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圖:《仁波切之殤——祭被囚十三載,身亡中國監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一書,由雪域出版社於2015年9月26日在西藏國際研討會發佈。尊者達賴喇嘛為丹增德勒仁波切著轉世祈願文並賜序。唯色提供)
王力雄讓我去寄信。我多少有些心安。這麽多天,我像一個袖手旁觀的人眼看著王放下正在構思的寫作,把時間和精力都用在蒙冤的兩個藏人身上。寫文章。寫信。寫建議書。徵集簽名。打電話。找媒體。約見可以一起想方設法的朋友。等等。從12月5日起,他的這些努力導致了一樁原本可以成為石沉大海的秘密事件得以暴露,不但漢人、藏人、西方人,不但北京、達蘭薩拉、華盛頓,不但網路,不但廣播,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這兩個藏人的生命成為衡量人性、人權、法律、法制的尺度而受到關注。
可以設想王要為此承擔的風險,身為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同族人的我,應該分擔。
2002年12月15日
• 爆炸案
記得12月5日晚,在新浪網上看見一條消息:「製造成都天府廣場爆炸的兩名分裂分子被判死刑」。這一結果,對於既出乎意料又似在意料之中,但內心深處一直期待著轉機的我不啻悶棒一擊。王也看到了這條消息,早在上個月,我們還在甘孜州旅行時,他已經寫了一篇關於爆炸案的調查文章從康定寄往美國之音,期望這一案件「不應該黑箱操作,必須公諸於眾」,以免構成冤案。
更早是在今年4月上旬的一天,從海外網站獲悉在四川警方的偵破下,發生在4月3日成都天府廣場的爆炸案已破,作案者已被抓獲。令我驚訝的是,作案者竟是一個名叫洛讓鄧珠的藏人。更令我驚訝的是,這個爆炸案以及近兩年發生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另外六起長期未破的爆炸案,都被認為是由一人策劃並指使,而這個人恰是我認識的一位在藏地康巴一帶德高望重的活佛,也就是「兩名分裂分子」之一的阿安紮西。
一位年過半百、身穿絳紅色袈裟的僧侶浮現眼前。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見面時他說:「什麽是佛教?要人做好事不做壞事的宗教就是佛教。什麽是菩提心?有一顆熱愛眾生的心就是菩提心。作為六道輪回中的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修一顆好心。」我還記得最後一次見面時(在他被捕前半年)他說:「我的媽媽死了,我很傷心,我要為我的媽媽閉關一年,為她念經修法,祈禱她有一個好的來世。」
王也見過這位活佛。他在《活佛爆炸案》中寫到:「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安紮西其人,並且耳聞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帶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農村牧場講經傳法,從事眾多慈善事業,創辦孤兒學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橋,保護生態,教育百姓戒煙酒禁賭博不殺生。不少戒掉惡習重獲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視為再生父母。我曾去過他的住處,對他的生活清貧印象深刻。當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供養’,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
這樣一個出家人,誰會想到有一天他會突然有了另一個名字——恐怖分子?王說:「聽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連我在心理上都難相信,更不要說敬仰他的信眾。」然而審判已經宣佈,沒有比死刑更重的懲罰已經降臨,雖然丹增德勒仁波切因為死緩或許免於一死,而洛讓鄧珠若無上訴的機會就將人頭落地,難道我們就只能眼看著冤案有可能造成,無辜的生命被如此草菅?
可是又有誰能夠幫助身陷囹圄的他們?
2002年12月16日
•沉默
到處都是沉默。
藏區一片沉默。北京的藏人,我指的是那些在體制內的藏人,更是若無其事。六天前,跟單位(《西藏文學》)主編去藏學中心,晚上會餐,然後舞會。大多數都是藏人,見到幾個位置很高的藏人:斯塔,格勒,等等。會餐時都是各種酒,白酒、紅酒。歡聲笑語,諂媚作態。我冷眼旁觀,但因心中憤懣,終於喝醉。趁酒醉,我「大鬧」了舞會,指責這些吃官飯的藏人,不為被陷害的活佛說話。舞會不歡而散,我算是出了一口氣。
2002年12月17日
•和張老見面
上午八點多。王力雄、張祖樺、蕭瀚、我,去北京某酒店見律師張思之先生。
張老據說是中國人權案的第一律師。但在見他之前,對他是否願意接受阿安紮西案並無太大把握。王認為這個案子的難辦程度幾乎不可能,因為所要面對的是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長、政治局委員周永康,而這個案子是周接手公安的第一個政績。
因蕭瀚記錯見面地點,張老和我們各在一處等候,足足遲了近二十分鐘才碰上,差一點失之交臂,這是不是預兆這件事情將有波折?
出乎意料的是,張老一說話,其口氣已儼然是阿安紮西案的律師,絲毫不必顧慮他是否願意接受。他的每句話都是職業律師處理案件的程式,井井有條。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否有救了呢?至少有希望不至於被冤枉。
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親屬阿珠仁波切聯繫上了。阿珠仁波切是阿沛•晉美通過美國的洛桑介紹的。他說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堂弟。他對突然出現的來自遠在北京的一些漢人的援助非常意外。我費了好大勁才說清楚這不是假的。
讓親屬簽名要求律師辦理案件的委託書,從張老的律師事務所傳真過來,然後給阿珠仁波切發過去了。我的藏話很糟糕,他們的漢話更糟糕,造成一些延誤。所幸發去的傳真他們還是收到了。阿珠仁波切派去了一個叫塔貝的人。
阿珠希望在委託書上簽名的是他的父親,也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父親的弟弟,這當然可以,只要是親屬就能在委託書上簽字。他的父親叫自仁魯魯。
又一個出乎意外的是,居然在酒店碰見康巴商人旦巴達吉。看上去憨厚其實很精明的旦巴達吉表示對這個案子不知道。也不知道丹增德勒仁波切。但他還是答應替我跟阿珠仁波切通電話。他流利的康巴話倒是說得很清楚。
看來還是很順利。這是不是預兆事情終究有個好的結果?在拍攝合影之前,聽見王說一句話:「妙手著文章,鐵肩擔道義」。知道他是在講在建議書上簽名的事情。有這樣的知識份子,如口口聲聲講中國應該出現哈威爾和曼德拉的秦暉,總是談論法國大革命的朱學勤等等,當真正在面臨的時候卻不發一言,不知道是表示沉默還是置之不理。
張老接話:「我們都不是鐵肩,其實是豆腐肩」。(免于恐懼的自由)是的,誰不恐懼失去自由?誰在這樣的權力之下不是豆腐肩?可是,就有這樣的豆腐肩在承擔鐵肩所要承擔的事情!所有的西藏人都應該向他們致敬!我很慚愧沒有帶來哈達。
身陷囹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是否會想到,有這麽一群陌生的異族人在為他們的生命奔走呼告?這是什麽樣的關係呢?前世的因緣嗎?張老說:「我相信這一點。我相信緣分。」
•捐款
王給我一個筆記本,讓記錄在辦理這件事情時的有關花費。在「收入」一欄,記下了他和張祖樺的名字。他們兩人一人捐款1000元。
•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親屬通話
下午和晚上,跟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親屬通了幾次電話。大多是那個叫塔貝的接的。塔貝的漢話還可以。當然是那種康巴口音的四川話。這種話我沒問題。
張老建議給洛讓鄧珠的親屬也發去委託書。兩個人的案子放在一塊辦理更為有利。是這樣的,否則洛讓鄧珠若被殺,就成了殺人滅口,就有死無對證的可能性,丹增德勒仁波切更是難以解脫。
塔貝告訴了不少情況。
一是說洛讓鄧珠。他說洛讓鄧珠是雅江四區的人,有老婆和孩子。他家裡很窮,住在牛場上,住的很遠。還說他不是活佛的親戚,因為活佛是理塘人,在雅江沒有親屬,塔貝他們都不認識他。但是,L和H都說洛讓鄧珠的確是活佛的親戚,是活佛已故父親那邊的親戚。
二是說一審判決的情況。在審判前,當地通知親屬去康定州法院參加旁聽。要求去三個人,但只批准了兩個人,一同去的還有理塘縣的七名幹部,塔貝說是工作組的。看來理塘縣專門為此成立了工作組,或者專案組。
塔貝說,在現場旁聽的兩個親屬回來後講,活佛和洛讓鄧珠是一起被帶上法庭的。活佛的身體看來很差,大不如從前,用塔貝的話來說,「活佛的身體垮了,垮得很凶」。當法庭宣讀了審判書之後,「活佛和洛讓鄧珠不服,當場都鬧起來了。活佛說,這些都是假的,他沒有乾過爆炸的事情,他是被人害的。他還大聲地喊了‘達賴喇嘛萬歲’。洛讓鄧珠很氣憤,也大聲地喊了‘達賴喇嘛萬歲’、‘阿登彭措萬歲’。」塔貝說,「有十多分鐘的樣子,坐在法庭裡的十幾個幹部一句話都不說,你看我,我看你,後來有一個女的,喊把他們兩個帶走,活佛和洛讓鄧珠就被四個員警帶走了。」塔貝說,去旁聽的兩個親屬很傷心,但是也不敢說,更不敢鬧。據說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被關押在康定,州公安局監獄。
塔貝說活佛被抓時他們找過當局,希望按照法律實事求是地調查這件事。如果活佛真的策劃了爆炸案,那他們也就沒有說的,也就認了。但是如果活佛沒有做過這種事,那就是冤枉,應該放人。他們要求請律師。最早當局答覆他們說,一定會實事求是地辦案的。律師可以請。可是後來又說,這個案子是反革命案件,不能請律師。
我轉告塔貝。一是要去找到洛讓鄧珠的親屬,也要在委託書上簽名,不會寫字找人代寫,然後按手印。二是要去康定,從州法院爭取拿到判決書,拿到之後告訴他們已在北京請了律師。還要要求見活佛,如果見不到儘量多瞭解活佛以及洛讓鄧珠的情況。
還轉告了不必擔心律師的費用,但塔貝表示他們親屬可以付費。當轉告他這邊已經有人捐款,他很吃驚,一直說謝謝。他們無法相信但這卻是事實。而他們只能對這些陌生的人說謝謝。幾乎每說一句話都要說一聲謝謝。
明天上午他們將發兩份傳真:自仁魯魯的身份證影本,有關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文件。
•打電話
X說,聽到判決後,雅江縣的人似乎沒有像剛聽說活佛被抓時那麽驚訝,好像很澹漠,不太關心了。另外,聽說宣判那天,康定街上有警報響,還聽說洛讓鄧珠已經被立即執行槍決了。X的消息並不準確,而且他說的縣裡的反應不過是縣裡那些幹部的反應。
•擔心
王晚上出門。十二點還不歸。開始擔心。想到廖亦武失蹤一夜,正是與在建議書上簽名有關,正是跟王這次去成都有關。
可能是12月13日晚上失蹤的。王怡說當時他們在喝茶,已被盯上。在場的還有冉雲飛和杭州的兩個人。分手之後廖亦武騎車回家,卻沒有到家,晚上宋玉打電話找廖亦武,但廖亦武第二天中午才回家。說是被關了一夜。
王怡還說第二天上午送杭州兩朋友去機場,在機場被查得很嚴,昨天在茶館遇見的盯梢他們的一個人也在場。看來四川已經在注意建議書引起的反應,開始調查。
十二點半王回來。帶來蕭瀚和女友的捐款2000元。
2002年12月18日
•傳真
昨天說好9點半塔貝發傳真過來,但等到10點還沒有,擔心他們已被注意,甚至更嚴重。打電話過去,還好,是塔貝接的。說理塘太冷,10點郵局才開門。
收到傳真。一是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簽名的授權委託書,二是昨天簽名的委託人自仁魯魯的身份證影本。
【授權委託書
委託人:阿安紮西
委託事項:就其委託人涉嫌犯罪一案特委託,理塘縣高成鎮民樂村居住的,委託人的叔叔自仁弄阿,理塘縣高成鎮民樂村居住的,委託人的表弟自仁弟弟,理塘縣高成鎮民樂村居住的,委託人的堂弟阿呷魯日(魯)為委託人聘請一名律師,為其辯護。
委託人:(阿安紮西藏文名和手印)
二00二年六月六日】
又發去傳真六份。是關於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的委託書。一式三份。但塔貝收到四份,不過不要緊。
和塔貝兩次通話。又得知一些情況。
塔貝是阿珠仁波切的妹夫。做生意的。自仁魯魯是他們的父親,63歲。他說六月份州公安局的一個局長告訴他們可以為丹增德勒仁波切請律師,還交給他們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簽名的授權委託書。他們於是準備請律師。本來想請成都的律師,但很多人都說請律師的費用很貴,有人說高達上百萬。這讓他們很為難,因為他們出不起這麽多的錢。但他們還是在想辦法找律師,可是甘孜州法院告訴他們,阿安紮西是反革命,不能請律師,所以他們就沒有再找律師了。
授權委託書上的三個人,自仁弄阿已去印度,自仁弟弟不在理塘城裡,在鄉下;阿呷魯日(魯)好像也出了一點事情,又說他不會願意當委託人,可能出於害怕。自仁魯魯是前兩人的兄弟,他願意當委託人。
至於找洛讓鄧珠的親屬很困難。一是不認識,二是他們去找的話也許不被同意。還說洛讓鄧珠不是活佛的親戚,他很有可能是害活佛。我告訴塔貝,不管再難也要儘量找到洛讓鄧珠的家人,否則洛讓鄧珠被殺對活佛更加不利。塔貝稱是。
另外,要去康定的話,塔貝說必須得經過理塘縣公安局的批准,否則不讓去,若是私自去就會被抓。塔貝說這是理塘縣公安局警告他們的,所以上午他去公安局找人批准他們去康定,但沒人上班,他表示下午還要去找。
他說,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們家裡的人一天到晚就曉得哭,沒有辦法。我們不相信活佛會做這種事。他是佛教徒,佛教徒怎麽會乾這種事?他做的事情都是勸大家不要喝酒,不要抽煙,不要打架,不要乾壞事。他沒有說過政治上的什麽話。現在這樣子對待他,我們不相信,很難過,我們要求實事求是。
•理塘縣公安局的命令
下午塔貝又去公安局,但是局長和副局長都不在,據說去康定好幾天了,不知道什麽時候回來,也許就在這兩天。
塔貝說是局長警告他們的。局長說只要你們去康定就要到我這裡來報到,我們批准了才能去,不然就要把你們抓起來。局長是藏人。
我把王的話轉告塔貝,既然如此,趕緊先去雅江找洛讓鄧珠的親屬在委託書上簽字,王很細心,連用黑色的簽字筆簽字,如果不會寫字就按手印等細節都考慮到了。
塔貝說就是,我們明天就去。其實洛讓鄧珠跟活佛不是親戚,我們一點兒不曉得他的情況,不過我們已經在街上找到了一個知道洛讓鄧珠家裡的女人。
•張老張律師
看張思之老先生的書:《我的辯詞與夢想》。
•告訴季丹
在王的再三催促下,終於找到季丹。告訴她代她簽名的事情,感覺很不好意思,竟然在她不知道整個事情原委的情況下就代她簽名,其實這樣很不好。但季丹說她會簽名的,沒關係。還說,還以為是要她去拍片呢。這倒是一個好主意,王說。
•是否上訴?
晚上王收到阿沛•晉美的信,信上說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並沒有上訴,此案已交四川省高法,轉入覆核程式。說此消息來自甘孜州法院的一個姓康的女法官。
這是不好的消息。王給張律師打電話。張律師說這就不好辦了,如果不提出上訴,律師就沒有理由介入案件。
王讓我趕緊打電話與甘孜州那邊聯繫。
C的手機是空號。Y的手機雖然通了,但聽不太清楚,不過他說他聽說提出上訴了。又給D打電話,D說他不清楚,但是他可以去打聽,然後再回話。還是要找到C,這次打通了。C像是正在一個聚會的場合,不過還是告訴我了很重要的情況。他說,阿安紮西提出了上訴,但洛讓鄧珠沒有提出上訴,洛讓鄧珠說判他死刑他「高興得很」。還說案子已經上交省法院,要覆核。至於是否執行判決還得有一段時間。
看來洛讓鄧珠是想求死了。真可憐。他或者是被屈打成招,或者是被栽贓,但對這樣的結果——讓仁波切受如此大的罪——他一定覺得無顏再活,生不如死。
王給張律師打電話。張律師一聽就說有轉機,只要有人提出上訴,整個案件就可以重新審察,繼而案件所涉及的人也得重新審察,這樣洛讓鄧珠的案子也可以隨之一起審理。
Y打來電話,他在海螺溝,他說他問過了,確實已經提出了上訴。但他說得沒有C詳細。
又給塔貝打電話,要求他們明天就去雅江找洛讓鄧珠的親屬,塔貝說明天一早就去,儘早趕回來,最遲後天發來傳真。
•散步
深夜的北京很冷。走在河邊,河面上已是積雪覆蓋著冰層。王說,應該把這件事情,從三年前(對於我來說是四年)開始記敘,一直到現在,以及將來的結果。這將是一部悲壯的書,比寫小說有價值。
2002年12月19日
•廖亦武再次被傳訊
王收到王怡信,說廖亦武今淩晨被抄家,又被帶去審訊,回家後被警告不准出去。
給廖亦武打電話,我稱他是「氣衝衝」,這是他在網上的名字吧?廖亦武告訴王,他的電腦也被抱走了。
廖亦武真夠不幸,據說原因似乎是關於16大的簽名。很難說不會輪到我們頭上。
•到底有沒有上訴?
王收到阿沛•晉美信,說沒有人上訴。這是怎麽回事?得弄清楚。
給C打電話繼續追問有無上訴這回事。C對我用手機很擔心,認為不安全,不過還是告訴我,有人上訴了,他看見過上訴書。問是誰上訴,他沒敢說阿安紮西,而是說紮西。還說另一個人沒有上訴。C說二審的時間至少是一個半月,覆核的時間也比較長,長達一年的也有。
但王說,張律師講過二審甚至半個月的也有,只要殺人更有利,這時間不會長的。
王接到電話,是《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告訴他確實有人上訴。
•碰見馬容
上網,碰見馬容。馬容問這個案子,還說本來法師也想要簽名的,但馬容有顧慮,所以勸法師不要簽名。我讓馬容感謝法師。
不過王的說法也很有道理。王說佛教僧侶其實應該簽名支持的。不管是藏傳,還是漢傳,都應該站出來呼籲。一個出家人如果都看不開,瞻前顧後,那還是什麽出家人?王說已經有人在問,為什麽沒有一個僧侶敢於簽名?
•D電話
D打我的手機。告訴我,沒有人上訴,說這個消息基本上確實。他在成都。
•塔貝沒有回來
給理塘打電話。一個滿口牛場話的女人告訴我,阿珠和塔貝都不在家,街上去了,今晚不回來,讓我明天再打電話。看來他們是去雅江找洛讓鄧珠的親屬了。這很好。
2002年12月20日
•法國廣播電臺
下午五點半的法國廣播電臺說,歐洲議會要求中國重新審理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認為證據不足。
•塔貝來電話
•恐懼
六點半,郝阿姨電話,說王有同學找。但王去跑步了,我告訴她。
十分鐘後,有人打來電話,聽聲音很溫和,說找王有事情,問住在哪裡,我告訴他地址,還告訴他住在308。
七點剛過,王回來,剛說幾句,那個電話來了。王接電話,說完話後告訴我是安全局的,說那人說他是安全局的小張,要跟王聊一聊。我懵了,半天才反應過來,但不知道應該怎麽辦。
王就告訴我,三個小時不回來就做些什麽事情。然後王就下樓了。我傻傻的,不知道應該怎麽辦。我說我害怕,王說,劉曉波經常被叫去聊天,劉霞都習慣了。王說以後會經常遇到的。我不知道怎麽辦,傻乎乎的,看著王離我越來越遠。
關上門,我在屋子裡轉來轉去,然後坐在電腦前想繼續寫文革,希望這個動作抵消剛才發生的事情,就像是剛才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王不過出門去見朋友,或者去散步了。
這時候,郝阿姨打來電話,她就在樓下,她問王走了多久。我趕緊下樓,在雪地裡的一輛警車旁邊見到了郝阿姨。郝阿姨說這警車不會是來找王的吧。看來不像是。可是王現在去了哪裡?他們把他帶到哪裡去了?
郝阿姨說沒想到我們是在這種場合見面的。郝阿姨待我很好。我送她回家。郝阿姨要我見一見陳伯伯。陳伯伯也很好。我們說了會兒話,我就回來了。我跑著回到了屋子,屋子裡沒有王,我想哭可哭不出來。
九點多,我正想給王打手機,或者給祖樺打電話,王回來了。我跑過去抱住他,從未有過的心情只能用這樣一個詞形容:失而復得。
王輕描澹寫地說了幾句。說他和三個安全是在一個茶館談話的。他說他把他們教育了一番。他們只是不住地說,是,是。看來他們不敢動王,至少目前不敢。王叫的茶是菊花茶,因為這個茶最便宜。我責備他應該叫最貴的茶。王說那還不是納稅人的錢。(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資料來源:唯色